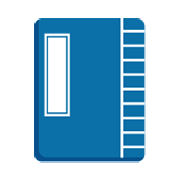评析
《毛诗注疏》:《维清》,奏《象舞》也。《象舞》,象用兵时刺伐之舞,武王制焉。○刺,七亦反。 [疏]“《维清》五句。”○正义曰:《维清》诗者,奏《象舞》之歌乐也。谓文王时有击刺之法,武王作乐,象而为舞,号其乐曰《象舞》。至周公、成王之时,用而奏之于庙。诗人以今大平由彼五伐,睹其奏而思其本,故述之而为此歌焉。《时迈》、《般》、《桓》之等,皆武王时事,成王之世乃颂之。此《象舞》武王所制,以为成王之时奏之,成王之时颂之,理亦可矣。但武王既制此乐,其法遂传于后,春秋之世,季札观乐,见舞《象》,是后于成王之世犹尚奏之,可知颂必大平乃为,明是睹之而作。又此诗所述,述其作乐所象,不言初成新奏,以此知奏在成王之世,作者见而歌之也。经言文王之法,可用以成功,是制《象舞》之意。○笺“象舞”至“制焉”。○正义曰:此诗经言文王,序称《象舞》,则此乐象文王之事,以《象舞》为名,故解其名此之意。《牧誓》曰:“今日之事,不愆于六伐七伐,乃止齐焉。”注云:“一击一刺曰一伐。”是用兵之时,有刺有伐。此乐象于用兵之时刺伐之事而为之舞,故谓之《象武》也。知者,以其言象,则是有所法象。《乐记》说《大武》之乐,象武王之伐,明此《象舞》象文王之伐。知武王制焉者,以为人子者贵其成父之事,文王既有大功,武王无容不述。《中庸》曰:“武王、周公,其达孝矣乎!孝者善继人之志,善述人之事。”明武王有所述矣。于周公之时,已象伐纣之功,作《大武》之乐,不言复象文王之伐,制为别乐,故知《象舞》武王制焉。武王未及太平而作此乐。一代大典,须待大平。此象文王之功,非为易代大法,故虽未制礼,亦得为之。周公大作,故别为武乐耳。《春官·大司乐》六代之乐,唯舞《大武》,以享先祖。此《象舞》不列于六乐,盖大合诸乐,乃为此舞,或祈告所用,《周礼》无之。襄二十九年,曾为季札舞之,则其有用明矣。案彼传云:“见舞《象箾》、《南籥》者。”服虔曰:“《象》,文王之乐舞《象》也。《箾》,舞曲名。言天下乐削去无道。”杜预曰:“箾舞者,所执南籥以籥也。”其言箾为所执,未审何器。以箾为舞曲,不知所出,要知箾与南籥必是此乐所有也。传直云“舞象”,“象”下更无“舞”字,则此乐名“象”而已。以其象事为舞,故此文称“象舞”也。《象舞》之乐象文王之事,其《大武》之乐象武王之事,二者俱是为象,但序者于此云“奏《象舞》”,于《武》之篇不可复言奏象,故指其乐名,言“奏,《大武》”耳。其实《大武》之乐亦为象也,故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、《明堂位》、《祭统》皆云“升歌《清庙》,下管《象》”。《象》与《清庙》相对,即俱是诗篇,故《明堂位》注“《象》谓《周颂·武》也”。谓《武》诗为《象》,明《大武》之乐亦为象矣。但《记》文于“管”之下别云“舞《大武》”,谓《武》诗则箫管以吹之,《武》乐则于戚以舞之,所以并设其文,故郑并《武》解其意。于《文王世子》注云:“《象》,周武王伐纣之乐也,以管播其声,又为之舞。”于《祭统》注云:“管《象》,吹管而舞《武象》之乐也。”皆《武》诗、《武》乐并解之也。必知彼《象》非此篇者,以彼三文皆云“升歌《清庙》,下管《象》”,若是此篇,则与《清庙》俱是文王之事,不容一升一下。今《清庙》则升歌,《象》则下管,明有父子尊卑之异。《文王世子》于升歌下管之后,覆述其意云:“正君臣之位,贵贱之等,而上下之义行焉。”言君臣上下之义,明《象》非文王之事,故知下管《象》者,谓《武》诗,但序者避此《象》名,不言象耳。 维清缉熙,文王之典。典,法也。笺云:缉熙,光明也。天下之所以无败乱之政而清明者,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。文王受命,七年五伐也。○缉,七入反。熙,许其反。 [疏]“维清缉熙”。○正义曰:诗人既睹太平,见奏《象舞》,乃述其所象之事,而归功于文王。言今日所以维皆清静光明无败乱之政者,乃由在前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。其伐早晚为之,乃本受命始为禋祀昊天之时,以行此法,而伐纣之枝党。言其祭天乃伐,其法重而可遵,故至今武王用之,伐纣而有成功,致得天下清明。是此征伐之法,维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矣,故武王述其事而制此舞,诗人见其奏而歌之焉。此“维清缉熙”是当时之事,作者先言时事,然后上本文王,又据文王说之而下,故其言不次。○传“典,法”。○正义曰:《释诂》云:“典、法,常也。”俱训为常,是典得为法。○笺“缉熙”至“五伐”。○正义曰:《释诂》缉熙皆为光也,但光亦明也,故连言之。无败乱之政而清明者,虽伐纣之后,亦得为此。言要大为清明,必是太平之世。此当是周公、成王之时,见其清明,乃上本文王也。文王七年五伐,即《尚书传》所云“二年伐于刂,三年伐密须,四年伐犬夷,五年伐耆,六年伐崇”是也。 肇禋,肇,始。禋,祀也。笺云:文王受命,始祭天而枝伐也。《周礼》以禋祀祀昊天上帝。○肇音召。禋音因,徐又音“烟”。 [疏]传“肇,始。禋,祀”。○正义曰:“肇,始”,《释诂》文。又云:“禋、祀,祭也。”是禋祭为祀。○笺“文王”至“上帝”。○正义曰:禋者,祭天之名,故云“文王受命,始祭天而枝伐”。《中候·我应》云:“枝伐弱势。”注云:“先伐纣之枝党,以弱其势,若崇侯之属。”是枝之文也。文王祭天,必在受命之后,未知以何年初祭。《皇矣》说伐崇之事云:“是类是祃。”类即祭天也。伐崇之后乃称王,应伐崇之时始祭天耳。五伐容有未祭天而已伐者,但所伐唯崇为强,言祭天而伐,据崇为说也。《我应》云:“玄汤伐乱崇㜸首。王曰:‘于戏!斯在伐崇谢告。’”注云:“斯,此也。天命此在伐崇侯虎,谢百姓,且告天。”是祭天而伐,主为崇也。引《周礼》者,《大宗伯》文,引之以證禋为祭天也。文王之时,禘郊未备,所祭不过感生之帝而已。引昊天上帝者,取禋祀之成文。彼又云:“祀五帝亦如之。”虽祭感生帝,亦用禋也。 迄用有成,维周之祯。迄,至。祯,祥也。笺云:文王造此征伐之法,至今用之而有成功,谓伐纣克胜也。征伐之法,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。○迄,许乞反。祺音其,《尔雅》云同。徐云:“本又作祯,音贞。”与,崔本同。 [疏]传“迄至祯祥”。○正义曰:“迄,至”,《释诂》文。“祺,祥”,《释言》文。舍人曰:“祺福之祥。”厶氏曰:“《诗》云:‘维周之祺。’”定本、《集注》“祺”字作“祯”。○笺“文王”至“吉祥”。○正义曰:此诗之作,在周公、成王之时。以文王为古,故谓武王为今,自是辞相对耳,非言作诗之时为武王也。祥者,是征兆之先见者也。文王始造伐法,武王用以成功,是文王之法,为伐纣征兆,故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。 《维清》一章,五句。
《诗经通论》:维清 维清,句。缉熙文王之典。句。肇禋,句。迄用有成,维周之桢。「禋」字通韵;余字本韵。○赋也。 小序谓「奏象舞」,妄也。朱仲晦不从,以为诗中无此意,是已。然未尝深考而明辨之,则何以使后人不惑乎!今按其说,莫详于孔疏矣。孔疏本非辟序,今节录其说可为辟序用。其曰:「序者于此云『奏象舞』,于武之篇不可复言『奏象』,故指其乐名,言『奏大武』耳。其实大武之乐亦为象,故礼记文王世子、明堂位、祭统皆云『升歌清庙,下管象』,象与清庙相对,俱是诗篇,故明堂位注『象,谓周颂武也』。谓武诗为象,明大武之乐亦为象矣。但记文于『管』之下别云『舞大武』,谓武诗则箫、管以吹之,武乐则干、戚以舞之,所以并设其文。故郑并武解其意,于文王世子注云『象,周武王伐纣之乐也,以管播其声,又为之舞』,于祭统注云,『管象「管象」,原误作「象管」,今校改。,吹管而舞武、象之乐也』,皆武诗、武乐并解之也。必知彼象非此篇者,以彼三文皆云『升歌清庙,下管象』,若是此篇,则与清庙俱是文王之事,不容一升一下;今清庙则『升歌』,象则『下管』,明有父子、尊卑之异,文王世子于『升歌、下管』之后覆述其意,云『正君、臣之位,贵贱之等,而上、下之义行焉』,言君臣、上下之义,明象非文王之事,故知『下管象』者,谓武诗;但序者避此象名,不言象耳。」按孔说谓礼记诸篇「下管象」皆指武诗甚明。盖象者,象武王之武功也。且谓武诗为「象武」,可也,亦不得谓之「象舞」。盖用以为舞「舞」,原作「武」,体会语气改。,此后世事,当时原诗安得即以「舞」名乎!是武诗且不可谓之象舞,何况维清之诗于象舞何涉耶!诸儒好穿凿者误信序「象舞」之说,谓礼记诸篇所言「象」者即此篇,反以郑注为武诗及孔疏为非,此佞序之过也。郑注礼记皆是,独于此篇下云「象舞,象用兵时刺伐之舞,武王制焉」,似以用兵时刺伐属文王者,谬矣。文王虽未尝无武功,而武功岂足以尽文王!文王之德至矣,作乐象功,乃独象其刺伐耶!又仲尼燕居云「下管象武」,则直言武,此尤明證。而说者犹以「下管象」为句,「武、夏籥序兴」为句,斯诚何心哉!又墨子曰「武王因先王之乐,命曰象武」,董子曰「武王作象乐」,则象自属武诗而不可混入维清之诗明矣。
「缉熙敬止」,言文王也,故「缉熙文王之典」为句。若曰「维清缉熙」,则不类矣。且「清」字为起韵。
【维清一章,五句。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