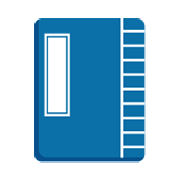评析
《毛诗注疏》:《维天之命》,大平告文王也。告大平者,居摄五年之末也。文王受命,不卒而崩。今天下大平,故承其意而告之,明六年制礼作乐。○维,《韩诗》云:“维,念也。”大音泰。后“大平”皆放此。 [疏]“《维天之命》八句”。○正义曰:《维天之命》诗者,大平告文王之乐歌也。以文王受命,造立周邦,未及大平而崩,不得制礼作乐。今周公摄政,继父之业,致得大平,将欲作乐制礼。其所制作,皆是文王之意,故以大平之时,告于文王,谓设祭以告文王之庙。言今己大平,己将制作,诗人述其事而为此歌焉。经陈文王德有余衍,周公收以制礼,顺文王之意,使后世行之,是所告之事也。○笺“告大平”至“作乐”。○正义曰:《乐记》云:“王者功成作乐,治定制礼。”功成治定,即大平之事。此经所云“我其收之,骏惠我文王”,是制作之意,明其将欲制作,有此告耳。制礼作乐,在六年之初,故知此告大平,五年之末也。又解所以必告文王者,文王受命,不卒而崩。卒者,终也。圣人之受天命,必致天下大平,制作一代大法,乃可谓之终耳。文王未终此事,而身已崩,是其心有遗恨。今既天下大平,成就文王之志,故承其素意而告之,冀使文王知之,不复怀怅故也。文王之不作礼乐者,非谓智谋不能制作,正以时未大平,故不为耳。今于五年之末,以大平告之,明己欲以六年成就之。言六年者,为制作成就之时,其始草创,当先于此矣。《明堂位》云:“六年制礼作乐,颁度量,而天下大服。”明是制作己就,故度量可颁,其礼亦应颁之,未即施用。《洛诰》说七年时事,周公犹戒成王,使肇称殷礼,祀于新邑,则是成王即政,始用《周礼》也。武王亦不卒而崩,惟告文王者,当时亦应并告,但以文王是创基之主,纣尚未灭,遗恨为深,周公之作《周礼》,称为文王之意,故作者主于文王,辞不及武王。序亦顺经之意,指言告文王焉。 维天之命,于穆不已。孟仲子曰:“大哉!天命之无极,而美周之礼也。”笺云:命犹道也。天之道于乎美哉!动而不止,行而不已。 [疏]“维天之命”。○毛以为,言维此天所为之教命,于乎美哉!动行而不已,言天道转运无极止时也。天德之美如此,而文王能当于天心,又叹文王,于乎!岂不显乎?此文王之德之大。言文王美德之大,实光显也。文王德既显大,而亦行之不已,与天同功,又以此嘉美之道,以戒慎我子孙,言欲使子孙谨慎行其道。文王意既如此,我周公其当敛聚之,以制典法,大顺我文王之本意。作之若成,当使曾孙成王厚行之,以为天下之法。周公以此意告文王,故作者述而歌之。○郑以纯为纯美,溢为盈,曾孙通谓后世之王,唯此为异。其大意则同。○传“孟仲”至“之礼”。○正义曰:文当如此。《孟子》云:齐王以孟子辞病,使人问。医来,孟仲子对。赵岐云:“孟仲子,孟子从昆弟学于孟子者也。”《谱》云:“孟仲子者,子思弟子,盖与孟轲共事子思,后学于孟轲,著书论《诗》,毛氏取以为说。”言此诗之意,称天命以述制礼之事者,叹“大哉,天命之无极”,而嘉美周世之礼也。美天道行而不已,是叹大天命之极。文王能顺天而行,《周礼》顺文王之意,是周之礼法效天为之,故此言文王,是美周之礼也。定本作“美周之礼”。或作“周公之礼”者,误也。《谱》云“子思论《诗》,‘于穆不已’,仲子曰‘于穆不似’”。此传虽引仲子之言,而文无不似之义,盖取其所说,而不从其读,故王肃述毛,亦为“不已”,与郑同也。○笺“命犹”至“不已”。○正义曰:天之教命,即是天道,故云命犹道也。《中庸》引此诗,乃云:“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。”是不已为天之事,故云动而不已,行而不止。《易·系辞》云:“日往则月来,暑往则寒来。”《乾卦·象》曰: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。于乎不显,文王之德之纯!假以溢我,我其收之。骏惠我文王,纯,大。假,嘉。溢,慎。收,聚也。笺云:纯亦不已也。溢,盈溢之言也。于乎不光明与,文王之施德教之无倦已,美其与天同功也。以嘉美之道,饶衍与我,我其聚敛之,以制法度,以大顺我文王之意,谓为《周礼》六官之职也。《书》曰:“考朕昭子刑,乃单文祖德。”○假音暇。溢音逸,徐云:“毛音谥。”慎,市震反,本或作“顺”。案《尔雅》云:“毖、神、溢、慎也。”不作“顺”字。王肃及崔、申、毛并作顺解也。明与音余。单音丹。 曾孙笃之。成王能厚行之也。笺云:曾,犹重也。自孙之子而下,事先祖皆称曾孙。是言曾孙,欲使后王皆厚行之,非维今也。○“厚之也”,一本作“能厚行之也”今或作“能厚成之也”。重,直龙反。 [疏]传“纯大”至“收聚”。○正义曰:“纯,大;假,嘉;溢,慎”,皆《释诂》文。舍人曰:“溢行之慎。”某氏曰:“诗云:‘假以溢我慎也。’”收者,敛聚之义,故为聚也。○笺“纯亦”至“祖德”。○正义曰:《中庸》引此云:“于乎不显,文王之德之纯。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,纯亦不已。”指说此文,故笺依用之。笺意言纯亦不已,则不训为大,当谓德之纯美无玷缺,而行之不止息也。《孝经》云:“满而不溢。”是溢为盈溢之言也。易传者,以下句即云“我其收之”,溢是流散,收为收聚,上下相成,于理为密,故易之也。文王既行不倦已,与天同功,是其道有饶衍,至于满溢,故言“以嘉美之道饶衍与我,我其聚敛之,以制法度”,谓收聚文王流散之德以制之也。其实周公自是圣人作法,出于已意,但以归功文王,故言收文王之德而为之耳。文王本意欲得制作,但以时未可为,是意有所恨。今既太平作之,是大顺我文王之本意也。欲指言所作以晓人,故言谓为《周礼》六官之职,即今之《周礼》是也。礼经三百,威仪三千,皆是周公所作,以《仪礼》威仪行事,礼之末节,乐又崩亡,无可指据,指以《周礼》,统之于心,是礼之根本,故举以言焉。引《书》曰者,《洛诰》文也。《书》之意,言周公告成王云:今所成我明子成王所用六典之法者,乃尽是配文祖明堂之人,文王之德,我制之以授子,是用文王之德制作之事,故引以證此。彼注云:“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,乃尽明堂之德。明堂者,祀王帝太皞之属,为用其法度也。周公制礼六典,就其法度而损益用之。”如彼注,直以文祖为明堂。不为文王者,彼上文注云:“文祖者,周曰明堂,以称文王。”是文王德称文祖也。彼注更自观经为说,与此引意不同,义得两通故也。○传“成王能厚行之”。○正义曰:传以周公制礼,成王行之,乃是为成王而作,故以《信南山》经、序准之,以曾孙为成王也。厚行之者,用意专而隆厚,即《假乐》所云“不愆不忘,率由旧章”是也。○笺“曾犹”至“维今”。○正义曰:笺以告之时礼犹未成,不宜偏指一人,使之施用一代法,当通后王,故知曾孙之王非独成王也。曾犹重也。孙之子为曾孙也。孙是其正称,自曾孙已下,皆得称孙。哀二年《左传》云:“曾孙蒯聩,敢告皇祖文王、烈祖康叔。”是虽历多世,亦称曾孙也。《小雅》曾孙唯斥成王,文各有施,不得同也。 《维天之命》一章,八句。
《诗经通论》:维天之命 维天之命,于穆不已,于乎不显,文王之德之纯!假以溢我,我其收之。骏惠我文王,曾孙笃之。无韵。或下二「之」字为韵。○赋也。 此亦祀文王之诗。小序谓「太平告文王」,乃赘语,盖欲切合「六年,周公制礼、作乐」之说也。凡祀告文王诸诗,孰非告太平乎!
此篇文气一直下,谓天命文王以兴周;文王中道而崩,天命久而不已,王其后世,乃大显文王之德,更以溢及于我;我今其承之,以大顺文王之德不敢违,而为曾孙者益宜笃承之也。欧、苏二氏皆如此解。上四句犹之「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。有周不显,帝命不时」,「天监在下,有命既集」,「有命自天,命此文王」诸语也。自中庸引用为说理之辞,于此诗上二句曰「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」,下二句曰「盖曰文之所以为文也,纯亦不已」,将「天命」与「文德」说作两事,谓「文王之纯」与「天之不已」无异,是为与天为一。按「天命」命字必不可作实字用,固已难通,详下。且前古之人从未敢以人比天,此自后世意见。中庸引诗断章取义,岂可据以作解!中庸亦在礼记中,凡礼记诸篇之引诗者可尽据以作解乎!前古之人又未尝深刻谈理,亦起于后世。必以「天命」与「文德」对,「于穆」与「不显」对,「不已」与「纯」对,有如是之深刻谈理者乎!自郑氏依中庸解诗,然于「天命」命字难通,乃训为「道」。嗟乎,诗之言「天命」者多矣,何以彼皆不训「道」而此独训「道」乎!欧、苏为前宋之儒,故尚能辟郑,不从其说,犹见诗之真面目;后此之人,陷溺理障,即微郑亦如释矣,况又有郑以先得我心,于是毅然直解,更不复疑。至今天下人从之,乃尽没诗之真面目,可叹哉!「假以溢我,我其收之」,左襄二十七年,引诗曰「何以恤我,我其收之」,杜预以为逸诗。然即此二句,非逸诗也。但古人引诗,原多异字,左传、礼记皆然,不可为据,自当依本诗作解,不必惑于所引诗也。「假」,使也。「溢」,欧阳氏曰「及也,如水溢而旁及也」,其解亦自明顺。集传曰:「『何』之为『假』,声之转也。」按「何、遐」为声之转,不闻「何、假」也。又曰:「『恤』之为『溢』,字之讹也。」据传以改经,失理甚矣!且不明标左传而若自为说者,更奇。烝民,宣王时之诗也,故予谓渐开说理之端。此诗周公作,岂亦说理乎!故中庸之说断乎不可用于此诗也。
【维天之命一章,八句。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