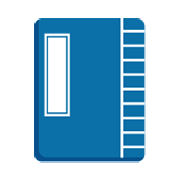评析
《毛诗注疏》:《桓》,讲武类祃也。桓,武志也。类也,祃也,皆师祭也。○祃,马嫁反。“桓,武志也”,本或以此句为注。 [疏]“《桓》九句”。○正义曰:《桓》诗者,讲武类祃之乐歌也。谓武王将欲伐殷,陈列六军,讲习武事,又为类祭于上帝,为祃祭于所征之地。治兵祭神,然后克纣。至周公、成王太平之时,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。序又说名篇之意。桓者,威武之志。言讲武之时,军师皆武,故取桓字名篇也。此经虽有桓字,止言王身之武。名篇曰《桓》,则谓军众尽武。《谥法》“辟土服远曰桓”,是有威武之义。桓字虽出于经,而与经小异,故特解之。经之所陈,武王伐纣之后,民安年丰,克定王业,代殷为王,皆由讲武类祃得使之然。作者主美武王,意在本由类祃,故序达其意,言其作之所由。讲武是军众初出,在国治兵也。类则于内祭天,祃则在于所征之地。自内而出,为事之次也。○笺“类也”至“师祭”。○正义曰:《释天》云:“是类是祃,师祭也。”《王制》云:“天子将出征,类乎上帝,祃于所征之地。”注云:“上帝,谓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。”言祭于南郊,则是感生之帝,夏正于南郊祭者。周则苍帝灵威仰也。南郊所祭一帝而已,而云五德之帝者,以《记》文不指言周,不得斥言苍帝,故漫言五德之帝以总之。又嫌普祭五帝,故言“南郊”以别之。五德者,五行之德。此五方之帝各有本德,故称五德之帝。太昊炎帝之等,感五行之德生,亦得谓之五德之帝。但类于上帝,谓祭上天,非祭人帝也。且人帝无特在南郊祭者。以此知非人帝也。谓之类者,《尚书》欧阳说以事类祭之,天位在南方,就南郊祭之。《春官·肆师》云:“类造上帝。”注云:“造犹即也。为兆以类礼即祭上帝也。”类礼依郊祀而为之者,言依郊祀为之,是用欧阳事类之说为义也。言为兆以祭上帝,则是随兵所向,就而祭之,不必祭于南郊。但所祭者,是南郊所祭之天耳,正以言造,故知就其所往为其兆位而祭之,不要在南郊。此言小异于欧阳也。南郊之祭天,周以稷配。此师祭所配,亦宜用常配之人,周即当以后稷也。祃之所祭,其神不明。《肆师》云:“凡四时之大田猎祭表貉,则为位。”注云:“貉,师祭也。于立表处为师祭,祭造军法者,祷气势之增倍也。其神盖蚩尤,或曰黄帝。”又《甸祝》“掌四时之田表貉之祝号”。杜子春云:“貉,兵祭也。田以讲武治兵,故有兵祭,习兵之礼,故貉祭祷气势之十百而多获。”由此二注言之,则祃祭造兵为军法者,为表以祭之。祃,《周礼》作“貉”,“貉”又或为“貊”字,古今之异也。貉之言百,祭祀此神,求获百倍。 绥万邦,娄丰年。笺云:绥,安也。娄,亟也。诛无道,安天下,则亟有丰熟之年,阴阳和也。○娄,力住反。亟,欺冀反,数也。下同。 [疏]“绥万邦”。○毛以为,武王诛纣之后,安此万邦,使无兵寇之害,数有丰年,无饥馑之忧。所以得然者,上天所命,命为善不解倦者以为天子。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,则能安有其天下之事,是其为善不倦,故为天所命。于是用其武事于四方,除其四方之残贼,能安定其家。谓成就先王之业,遂为天下之主。乃叹而美之,于乎此武王之德,乃明见于天。殷纣以暴虐之故,武王得用此美道以代之。○郑唯下二句为异。言于明乎曰天,言天道之大明也。纣为天下之君,但由为恶之故,天以武王代之。余同。○笺“绥安”至“阳和”。○正义曰:“绥,安”,《释诂》文。又云:“亟、屡,疾也。”同训为疾,是屡得为亟也。经言万国,笺言天下,天下即万国也。《尧典》云:“协和万邦。”哀七年《左传》曰:“禹会诸侯于涂山,执玉帛者万国。”则唐、虞、夏禹之时,乃有此万国耳。《王制》之注以殷之与周唯千七百七十三国,无万国矣。此言万国者,因下有万国,遂举其大数。此文广言天下之大,不斥诸侯之身,国数自可随时变易,其地犹是万国之境,故得举万言之。此安天下,有丰年,谓伐纣即然。僖十九年《左传》云:“昔周饥,克殷而年丰。”是伐纣之后,即有丰年也。 天命匪解。桓桓武王,保有厥士。于以四方,克定厥家。士,事也。笺云:天命为善不解倦者,以为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,则能安有天下之事。此言其当天意也,于是用武事于四方,能定其家先王之业,遂有天下。○解音懈。注同。 [疏]笺“天命”至“天下”。○正义曰:以“天命匪解”为下文总之。“克定厥家”,是天子之事,故知天命以为天子也。安有天下之事,谓天下众事,武王能安而有之,以天下为任,而行之不解,言其当于天意也。以当天意,故天命之,于是用其武事于四方,谓既能诛纣,又四方尽定,由是万国得安,阴阳得和。此言结上之意也。家者,承世之辞,故云能定其家先王之业,遂有天下。先王虽有其业,而家道未定,故于伐纣,其家始定也。 于昭于天,皇以间之。间,代也。笺云:于,曰也。皇,君也。于明乎曰天也,纣为天下之君,但由为恶,天以武王代之。○于音乌。注同,间,间厕之间。注同。 [疏]传“间,代”。○正义曰:《释诂》文。毛传未有以于为曰,皇多为美,此义必不与郑同也。王肃云:“于乎周道,乃昭见于天,故用美道代殷,定天下。”传意或然。○笺“于曰”至“代之”。○正义曰:“于,曰。皇,君”,《释诂》文。言于明乎曰天,言天去恶与善,其道至光明也。以武王代纣,即是明之事。言武王当天意以代,纣所以叹美之。 《桓》一章,九句。
《诗经通论》:桓 绥万邦,屡丰年。天命匪解。桓桓武王,保有厥士,于以四方。本韵。「邦」、「王」、「方」,叶。克定厥家,于昭于天,皇以间本韵,叶「天」。之。赋也。 小序谓「讲武、类、祃」,纯乎杜撰。又云「桓,武志也」,亦泛混。似亦因楚子以此篇为武之六章而云。集传谓此颂武王之功,固亦阙疑,然又曰「春秋传以此为大武之六章,今之篇次盖已失其旧矣」,嗟乎,何其无学识至于此也!左传杜注竟未曾阅,乃据楚乐章之篇次,见上。反疑诗之失旧乎!诗三百五篇经孔子手定,故曰「诗三百」,其无阙失可知。又曰「雅、颂各得其所」,则雅、颂尤自无阙失也。不然,何以云「各得其所」耶?楚子在鲁宣公时,孔子去宣公仅百一二十年,其间初无若秦火者,何以大武一篇仅存三章,而失其一、二、四、五四章乎?若然,孔子仅从阙失之余掇拾其残编断简而已,其何以明诗教于天下乎?可谓不察而妄谈矣。又曰「又篇内已有武王之谥,则其谓武王时作者亦误矣」,辨见武篇。且既以此为误,何以独信其前说乎?况乎以不误为误也!又曰,「序以为『讲武、类、祃』之诗,岂后世取其义而用之于其事也欤?」仍依恋于序而不忍置,故愚谓佞序者莫若朱也。
「间」,毛传曰「代也」。严氏曰「多方云:『有邦间之。』」,邹肇敏驳之曰:「按多方之诰曰:『乃惟有夏图厥政,不集于享,天降时丧,有邦间之。』盖言夏丧邦而殷代之,与此处『间之』不同。彼『之』字属夏,此『之』字属天。能左右之曰『以』。『于昭于天,皇以间之』,盖俨然以武配天也。愚意,桓诗即明堂祀武之乐歌。」此意亦新,存之。
【桓一章,九句。】